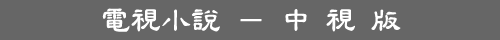
劇本原著:江佩玲、張瑞娟、景得編劇群/小說改寫:李旼
掃描:genesis/打字、校對:jiamin

「不好了,不好了,姑爺有麻煩了!」
小鈴子一大早就急匆匆地跑進花廳,口裡還大聲嚷嚷著。
「什麼事?瞧妳那失了魂的模樣!」婉兒正在台前梳妝,從鏡子裡望著小鈴子。
「臨安府派人來請姑爺過堂會審一件案子。」
小鈴子喘著氣回答,一旁的王魁竦然一驚。
「什麼案子妳知道嗎?」
「是……」小鈴子望了一下王魁說:「是來自建業的一男兩女呈狀告姑爺拋棄糟糠……。」
婉兒好似挨了一記悶棍,轉頭望向王魁。
該來的總是要來,只是沒想到來得這般快。原來春香說的玉石俱焚、同歸於盡就是這樁。
「怎麼回事?魁哥,告訴我,這是怎麼回事?你不是告訴我你是孑然一身,一無所有嗎?怎麼突然跑出一個糟糠之妻?這到底是不是真的?」
王魁平靜地說道:「貧在鬧市無人問,富在深山有遠親,我從一介窮書生考上了功名,前來攀親帶故或是訛詐騙錢的自然多了些。」
「嗯!」婉兒點點頭道:「爹爹以前官卑職小,根本無人聞問,一旦飛黃騰達當上丞相,瞧著吧,親戚朋友也不知從哪兒全冒出來了,這些人我見多了,魁哥你要小心應付。」
「這妳倒不用擔心,我自會便宜行事。小鈴子,臨安府的人呢?」
「臨安府的師爺正在大廳候著。」
「告訴他待本官換了冠帶立刻就到。」
王魁疾步往內堂而去。
臨安府正待開庭,桂英、春香和柱兒在堂外候傳。坐在牆角,柱兒沈不住氣,低聲說道:
「乾脆抖出姓王的底細,說他是王師松的二公子王仲平,看他承不承認。」
「千萬不可,」桂英說道:「這樣豈不是證明我們自己也有窩藏朝廷命犯之嫌,千萬不可莽撞!」
「對呀!對呀!我怎麼沒想到這點!」柱兒摸了摸頭。
春香接道:「說你是豬腦袋還不承認。」
堂鼓聲中,左右兩排衙役疾步就位。
師爺、府尹依序就位,向身旁就位陪審的王魁禮貌地點了點頭,王魁神情冷靜,卻透著幾許不安,只是沒人察覺罷了。
府尹一拍驚堂木:「帶原告焦桂英、丁寶柱、馬春香!」
桂英等一行在「威武」聲中從容上堂。行進間,桂英與王魁四目交投,只見她淚眼中恨火狂燒,王魁見狀,觸目驚心,問心有愧而本能地避開她的目光。
臨安府尹問道:「焦桂英、丁寶柱、馬春香你們三人狀告何人?究竟有何冤屈?」
桂英與王魁又一次四目交投,隨即應詢回話:
「回大人,民婦原是刑部尚書侍郎王魁的元配糟糠。」
堂外群眾一陣議論之聲。
府尹堂木猛拍:「肅靜!肅靜!」
「威──武──」轟喏聲中,群眾噤聲。
「焦桂英,說下去!」
桂英道:「王魁金榜高中後就貪圖榮華富貴,改娶崔相國之女為妻,民婦不服,曾於日前赴侍郎府投親,卻遭家院趕了出來。」
臨安府尹望了望王魁:「王侍郎,焦桂英果真是您元配之妻嗎?」
王魁目光投向台下的桂英:「本官與焦桂英雖是同鄉故交,但並無夫妻之誼。」說完,將目光掃向他方。
桂英聞言幾乎跪不住,直喘著大氣,柱兒和春香連忙將她扶住。
春香忿然地指著台上道:「王魁,你佔了便宜還賣乖,誰不知道你和桂英有夫妻之實。」
「大膽!」府尹一拍驚堂木:「竟敢對朝廷命官無禮,本府未曾問話於妳,不得任意開口,若是再咆哮公堂,本府就打妳二十大板,逐出公堂!」
春香只好噤聲,並狠狠瞪了王魁一眼。
「既然妳說是王大人的糟糠,可有人證、物證?」
「回大人,民婦是和王侍郎私訂終身,以天地為鑑,日月為憑,廟中土地可為證人……。」
堂外又是一陣鬨笑,柱兒急急說道:
「我和春香可做證人,飄紅院的護院、姐妹皆為證人。」
「那麼──證物呢?有無任何訂情之物可資證明?」
桂英內心劇烈掙扎了良久,當初王魁曾給了她一只王家的傳家髮簪,簪上雖有具名,卻刻著「王仲平」三字,然此時此刻卻不容許她拿出來用以佐證。
「台下可有人可以證明刑部侍郎和焦桂英是夫妻?」
台下眾人議論紛紛,卻沒有一人上來。
「只憑你三人一廂說詞,無媒無證,本官如何採信?」
這時,王魁平復了情緒,起身站了起來:
「本官不願為難這位姑娘,本官承認與焦桂英有夫妻之實……。
群眾再度嘩然,王魁卻又立刻朗聲壓過嘩然之聲:
「但是卻無夫妻之份!」
群眾又低聲開始議論,桂英氣得渾身發抖:
「王魁!你……你……」桂英一時為之氣結。
王魁不忍卒睹地別開視線,繼續說道:
「本官承認與焦桂英確有一段私情,然而那只是逢場做戲,不足一提……。」
台下跪著的三人,不相信地互望了一眼,桂英淚眼婆娑地說道:
「王魁,看著我,我要你看著我,親口告訴我,你跟我只是逢場作戲……?你是不是真的存心始亂終棄,不認我焦桂英為妻……?」
王魁聞言,心如刀割,但猶在遲疑,眾人亦摒息以待。
桂英雙目圓瞠,怒嗔道:「王魁,你不敢看我是不是?」
王魁只好再次與她四目相投,只見她淚流滿面,泣不成聲。
「告訴我!你我之間到底有沒有夫妻之份?」
王魁強忍著穿心之痛,朗聲說道:
「我王魁只有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,名字叫:崔──婉──兒!」
群眾大嘩,此時的焦桂英卻笑了,笑得全身發顫,笑得王魁渾身發毛。
「看錯了!我真的看錯你了,我該受制裁!」焦桂英徒然轉向府尹:「回大人,民婦招供。民婦得知昔日恩客王魁飛黃騰達之後,便前來投靠,索求不遂之下啣恨報復,借機誣陷申告,以圖洩憤,請大人治罪。」
春香、柱兒大驚,拉住桂英。
府尹將驚堂木一拍:「大膽焦桂英,妳敢啣恨報復,誣陷朝廷命官,如今真相大白,本府要將你三人以誣告之罪予以重責,來人啊!」
王魁連忙阻止道:「且慢,如今案情明朗,還我清白,本官不願再追究。請府尹大人賞我薄面,法外施恩,赦免他們三人。」
說完與府尹對看一眼,府尹自明其意。
桂英不可思議地看著王魁,淚水如決堤洪流,渾欲昏迷……。
「既然是王侍郎寬宏大量,不願追究,那麼就開赦爾等三人無罪,退堂!」
衙役們散班,群眾散去,柱兒和春香扶桂英緩緩起身,木然地立於大堂中央……。
王魁向堂外走去,與桂英錯肩而過,他熱淚上湧,內心痛愧不堪,卻是有口難言。
桂英亦悲恨交纏,淚流不止,含恨的目光目送王魁離去……。
王魁疾步走於路道上,目光盯著前面三個人影,他想奔向前去,又躊躇著不敢造次……。
「娘子,我公堂上所說的都不是真心話,可是我如果不這麼說,我勢必丟官待罪,前程盡毀……。娘子……妳聽我把事情始末對妳說清楚,好嗎……?」
前面三人愈走愈遠,王魁追上幾步,忽又佇足不前,搖搖頭,轉身疾步而去。
三人與王魁背道而行,越離越遠──
朔風野大,牧野蒼茫,心碎神傷的桂英立於土地廟前……。
「我只有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,名字叫崔婉兒──崔婉兒──崔婉兒──崔婉兒……。」
她心中一直迴盪著這句話,她抬頭望著土地公問:
「我這麼吃苦受罪,忍受著冷嘲熱諷,我日日地等,夜夜的盼,我等來的是什麼?我盼來的是什麼?」
「我只有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,名字叫崔婉兒──」
想不到,土地公回答她的也是這句話。
「天哪!長久的等待,結果我等來的就是這句話麼?」
她不斷地用手抓頭,血絲,順著指間流下。
「我當初真是鬼迷了心竅……我怎麼會去相信王仲平的虛情假意……?」
桂英的目光再度掃到土地公神像,她激憤地用手一指:
「我發現有件事很好笑,人人都相信神明,可是我提到你是我們的婚配證人,卻引得人們哈哈大笑,哈哈大笑,哈哈哈……」
桂英的情緒陷入崩潰,拾著香爐的碎片砸向神像,又將桌上所有的香燭供品掃倒在地,接著筋疲力竭地趴倒在桌上。
「轟──隆」一聲巨響,天上雷光閃電,桂英受驚地抬起頭,步步後退,眼睛望向屋樑……。
接著,桂英緩緩低下頭,緩緩解下腰帶,找來凳子,登了上去,再將腰帶往樑上一掛……。
一聲暴雷,廟外風狂雨急……。
書房中,王魁靜靜地翻著書,思緒早已不知飄向何方,渾然不覺婉兒在他身後將襖子往他身上一披。
「臘月近了,我要趕快把這件襖子做好為你穿上,來,站起來量量合不合身?」
王魁沒奈何地站起身子,由婉兒試著。
「哎!剛好合身耶!不長也不短。」
此時,小鈴子進來,對王魁欠了欠身,說道:
「姑爺!相爺請您過府喝茶!」
婉兒拉著王魁的手說:
「走!我也陪你過去喝茶。」
相爺府內,崔貴望著廳上的王魁和婉兒,高興地說:
「王魁!老夫得婿如此,夫復何求啊!」
王魁拱手道:「小婿年少輕狂,鑄下錯事,以至鬧得滿城風雨,令岳父大人蒙羞;小婿自知有罪,甘心領責,請岳父大人教訓!」
「賢婿說哪兒話,男人風月場所去去無傷大雅,勿須過份則可。只怪那名叫焦桂英的風塵女子太過痴情,竟然登堂入室找上門來,幸好賢婿有驚無險,全身而退,老夫應當辦桌酒席替你壓壓驚才是。」
王魁尷尬地笑笑:「豈敢!豈敢!」
「可憐喲,那名風塵女子……」崔貴似有所隱,突然住口不言。
「可憐什麼?」婉兒插口問道。
「那名女子自殺了。」崔貴搖搖頭歎息道。
「什麼?您說什麼?」王魁猛然抬頭。
「那名女子對賢婿太過痴情,聽說在土地廟裡上吊自盡了。」
王魁只感到一陣天旋地轉,周身發冷……。
他力持鎮定,想端茶盅喝口茶,不料雙手硬是不聽使喚,杯蓋、杯身、杯底被震得叮叮作響,茶水亦濺得一地。
王魁再也按捺不住,把茶放回几上:
「小婿身體不適,先行告退!」
背著崔貴說完兩句話,就猛然衝向門外。
他踉踉蹌蹌地步於廊間,幾次要抱住廊柱喘息,才能再掙扎著向前而去。
王魁奔入自己的房間,掩上門,他緊緊握住拳頭,猛力地咬著,企圖藉以抑制自己痛哭嘶吼的衝動。
「早知道這場官司會把妳逼死,我當初不如承認下來,娘子──桂英──我對不起妳……。」
王魁痛哭流涕,悔恨滿腔。
「如果報仇的代價是賠上娘子妳一條命,我寧可放棄報仇,和妳逃到天涯海角,天地之大,豈會無我倆容身之地?」
王魁雙手摀臉,身子一陣暈眩,砰然倒地。
王魁和婉兒的新房仍充塞著新婚的喜氣。
回到房裡,倒了杯水喝著,婉兒悄悄過來,猛一下從王魁身後摟住他的腰。
「嗯,怎麼有股女人香水的味道?」
王魁有些心虛,卸下婉兒的雙手走到一邊:「胡說,怎會有香水味?」
「咦,我的身上抹的是玫瑰花露,如果你身上沒有香水味,那才奇怪呢!」
王魁鬆了一口氣,登時換了一張笑臉迎向婉兒,摟住她的腰說:「我是個大男人,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總不好,我這就去洗個澡。」
「等一下!」婉兒伸手摸了摸他頸下的玉珮:「你這塊玉不拿下來嗎?」
王魁說道:「這是我自幼隨身佩戴的護身玉珮,平常連洗澡都不拿下來的。」
婉兒撒嬌地用臉蹭著他:「魁哥,你愛不愛我?」
王魁楞了楞:「當然愛啊!」
「有多愛?你願意用生命來愛我嗎?你肯為我而死嗎?」
王魁笑了笑說:「女人總是希望男人愛她愛到為她而死,但這不可能的,因為男人有太多的大事要去做……」
王魁說這話也是若有所指,婉兒當然聽不出來。
王魁把話鋒一轉說:「但是妳不是普通的女人,妳就是我的命脈,我當然可以為妳而死!」
婉兒反怒為笑:「我不要你為我死,我只要你給我這個東西。」
婉兒說著已握住那塊玉珮。
王魁只好自項間解下絲線:「好吧,這玉又沒有什麼價值。」
婉兒早已拉開項間衣服:「我要你親手替我繫上。」
王魁只好面對婉兒,為她繫上那玉珮。婉兒順勢偎入他懷中,緊緊抱住他的身子,臉上充滿幸福的笑容;王魁臉上,卻是一片冷漠。
「閨中少婦不知愁,春日凝妝上翠樓,忽見陌頭楊柳色,悔叫夫婿覓封侯。」
婉兒獨守著空閨,沒事找本書看看,偏偏讀到自己不喜歡的句子,氣得把書一丟。接著拿著女紅做針黹,卻又刺到手,只好把指頭含在口中吸著、吮著……。
她的目光掃向枕席,伸手摸了摸寒涼的棉被,眼窩泛紅,她先是開始流淚,最後終於抽抽嗒嗒地哭了起來。
這時,崔相爺突然走了進來。
「婉兒,妳怎麼啦,是王魁欺負妳了?」
「沒有!沒有……」婉兒忙著否認。
「妳明明哭過……」
「女兒剛才被針扎到手指,很痛,所以才……。」
「婉兒,我問妳,妳要跟爹說老實話。」
崔貴坐到女兒的床沿,關切地問:
「王魁是不是常常花天酒地、深夜不歸,把妳冷落一旁?」
「沒有,相公沒有花天酒地,也沒有冷落我……。」
「那麼……是我底下的那些人看錯囉?」崔貴盯在女兒臉上瞧著:「他們告訴我侍郎經常在外頭喝得爛醉如泥,徹夜留連在外。」
婉兒強忍著淚:「爹,沒有的事,魁哥怎麼會辜負我?他對我百般疼惜,呵護備至,甚至可說是愛若珍寶、視如己命,您看!」
婉兒自頸項內拔下那塊玉珮。
「這是他從小貼身所繫的護身玉珮,他都送給女兒了。」
崔貴見那玉珮,神色突然一變,連忙接過來仔細辨視,不禁暗自驚駭:「這正是當年老夫贈與王師松次子的彌月之禮,難道王魁就是……王仲平?」
崔貴驚出一身冷汗。
~第四章完~




